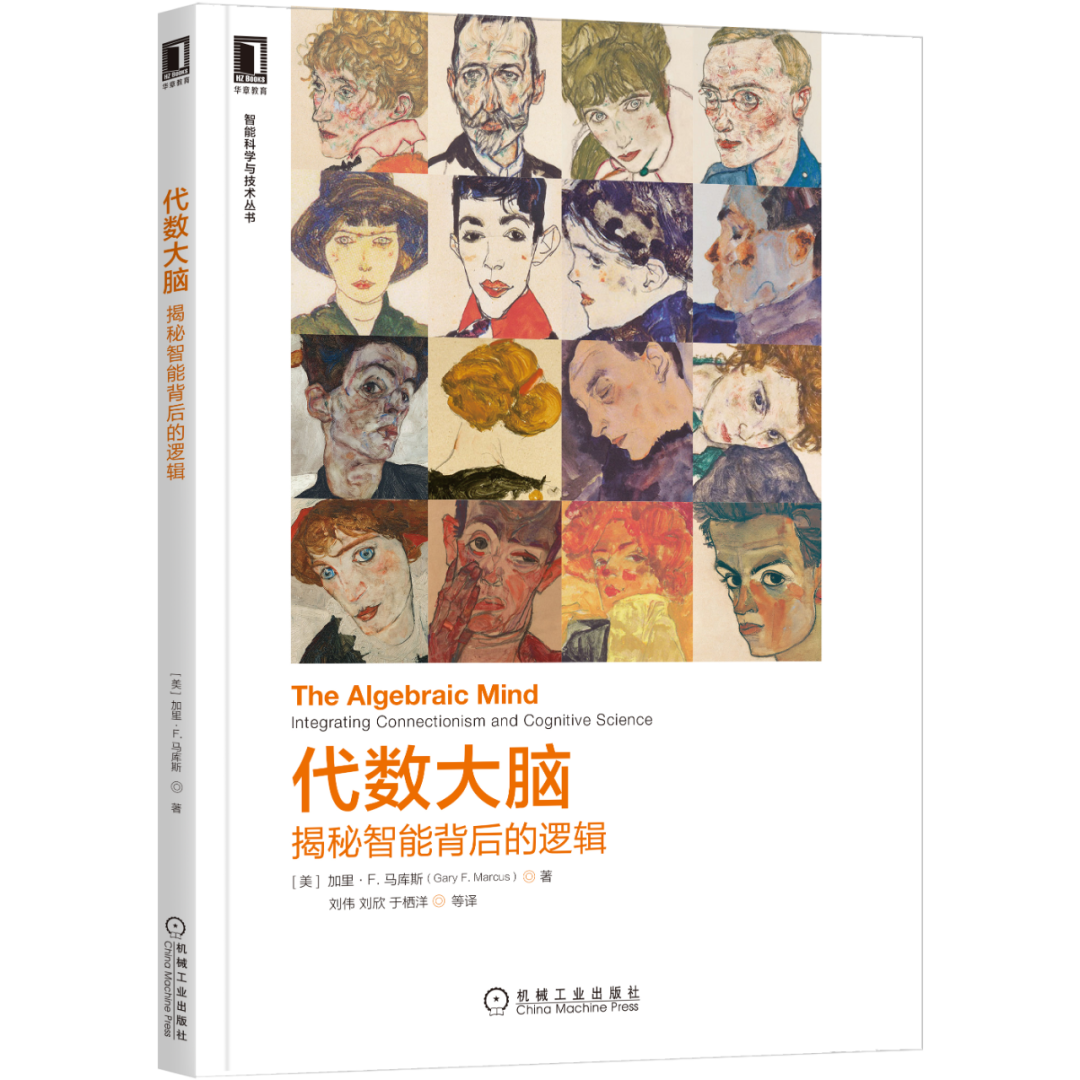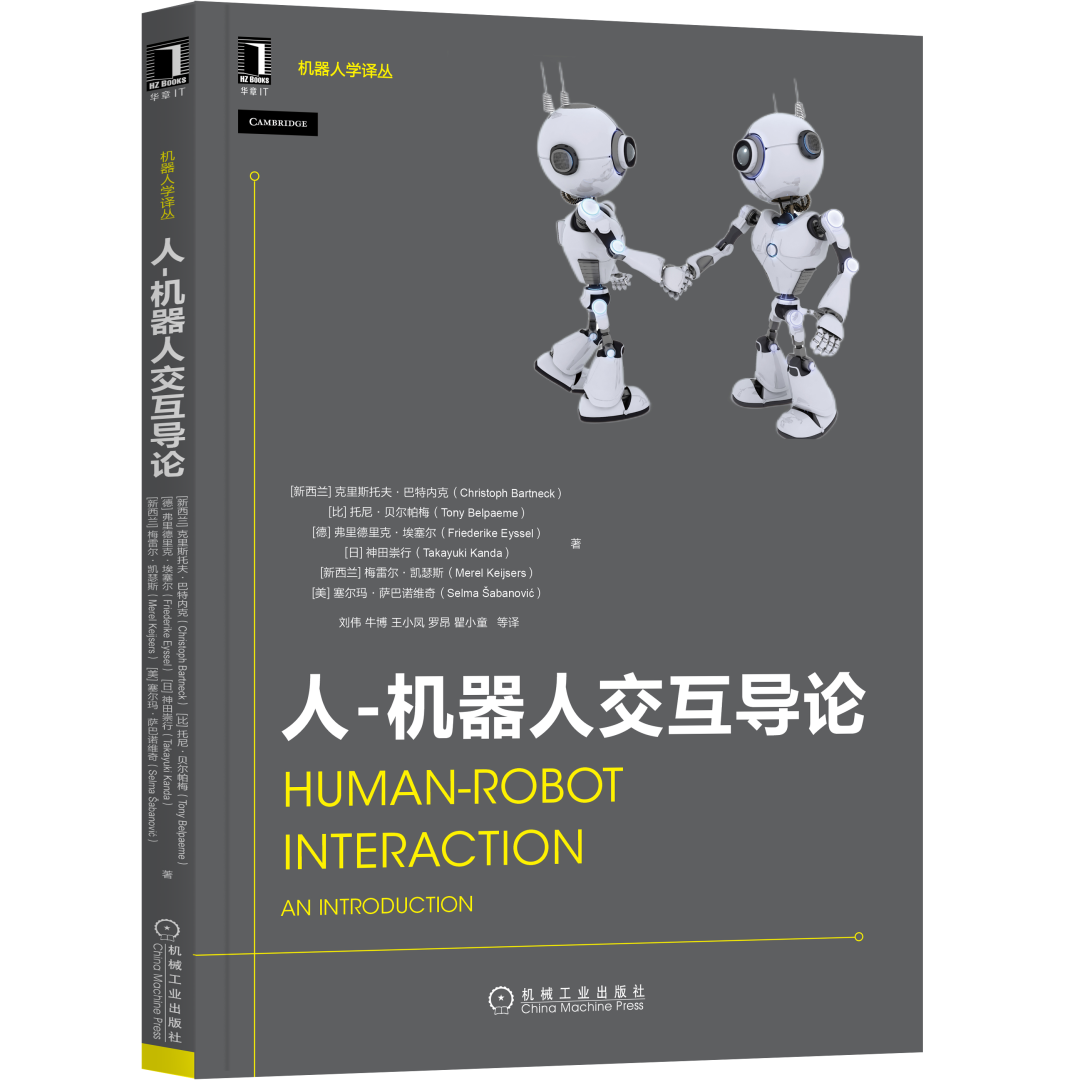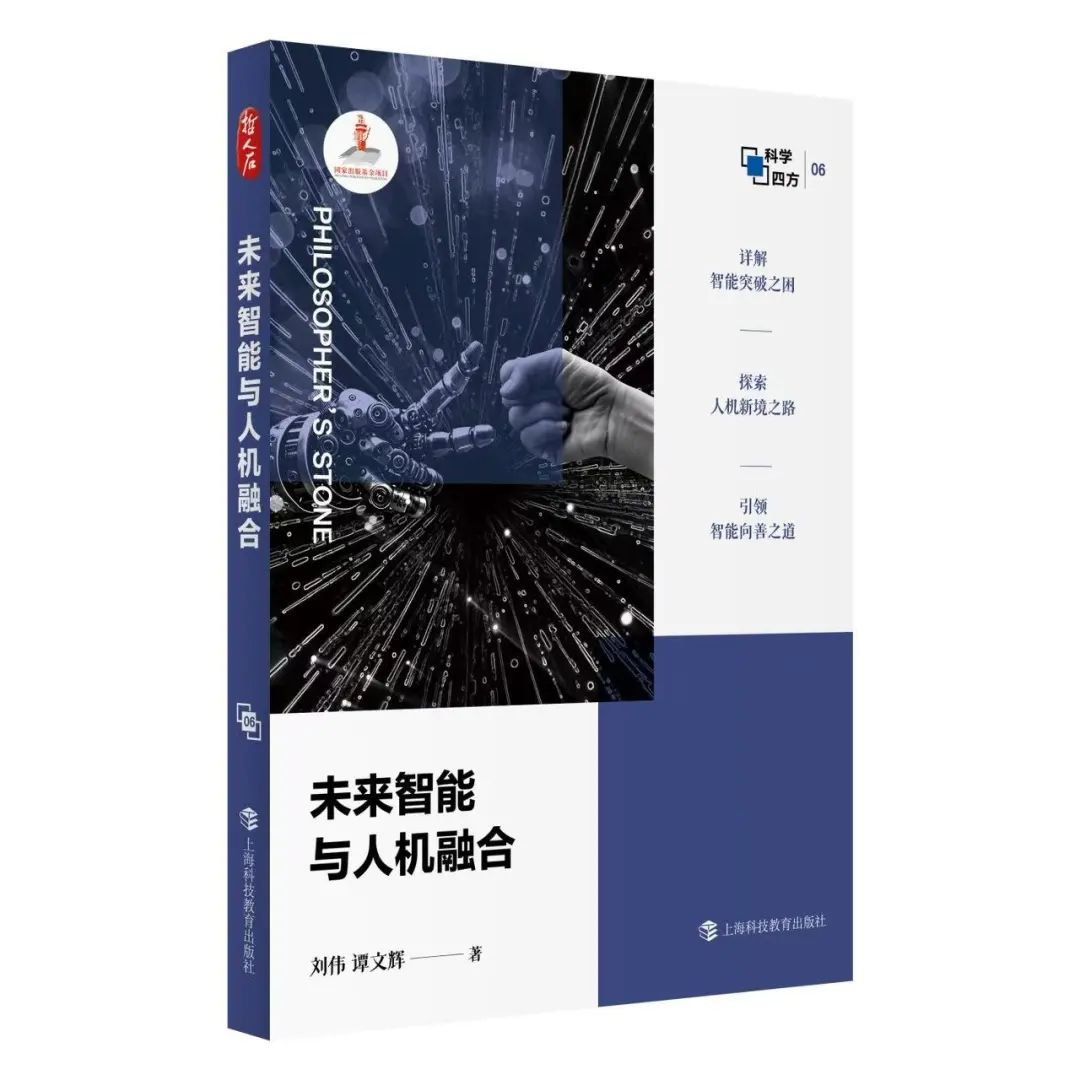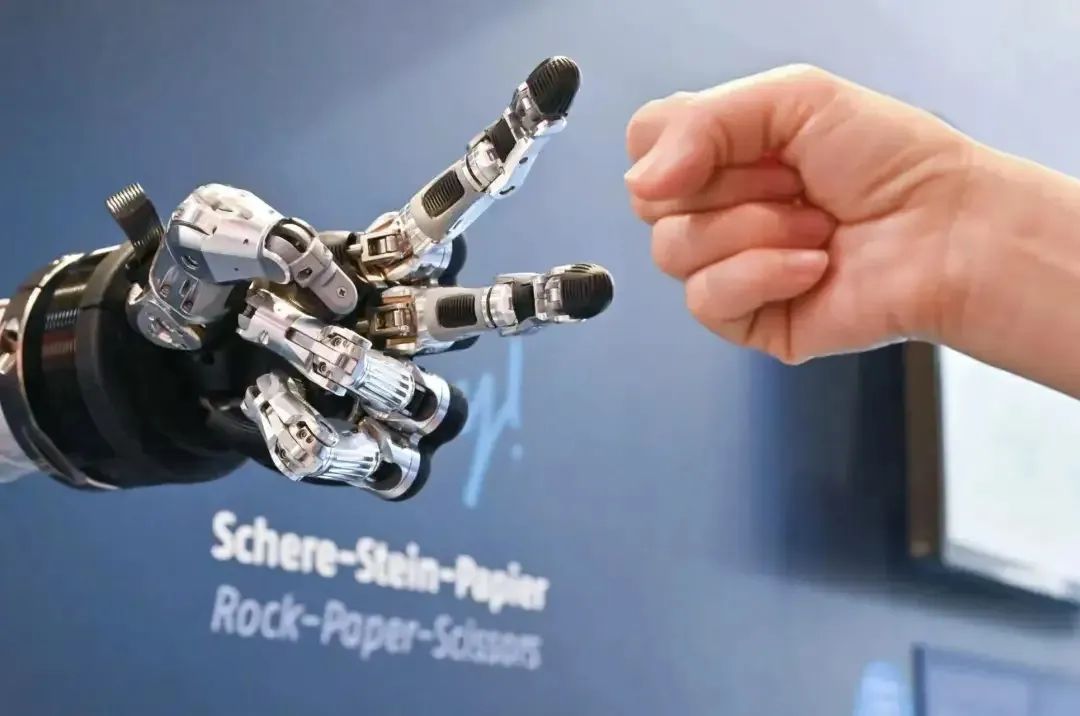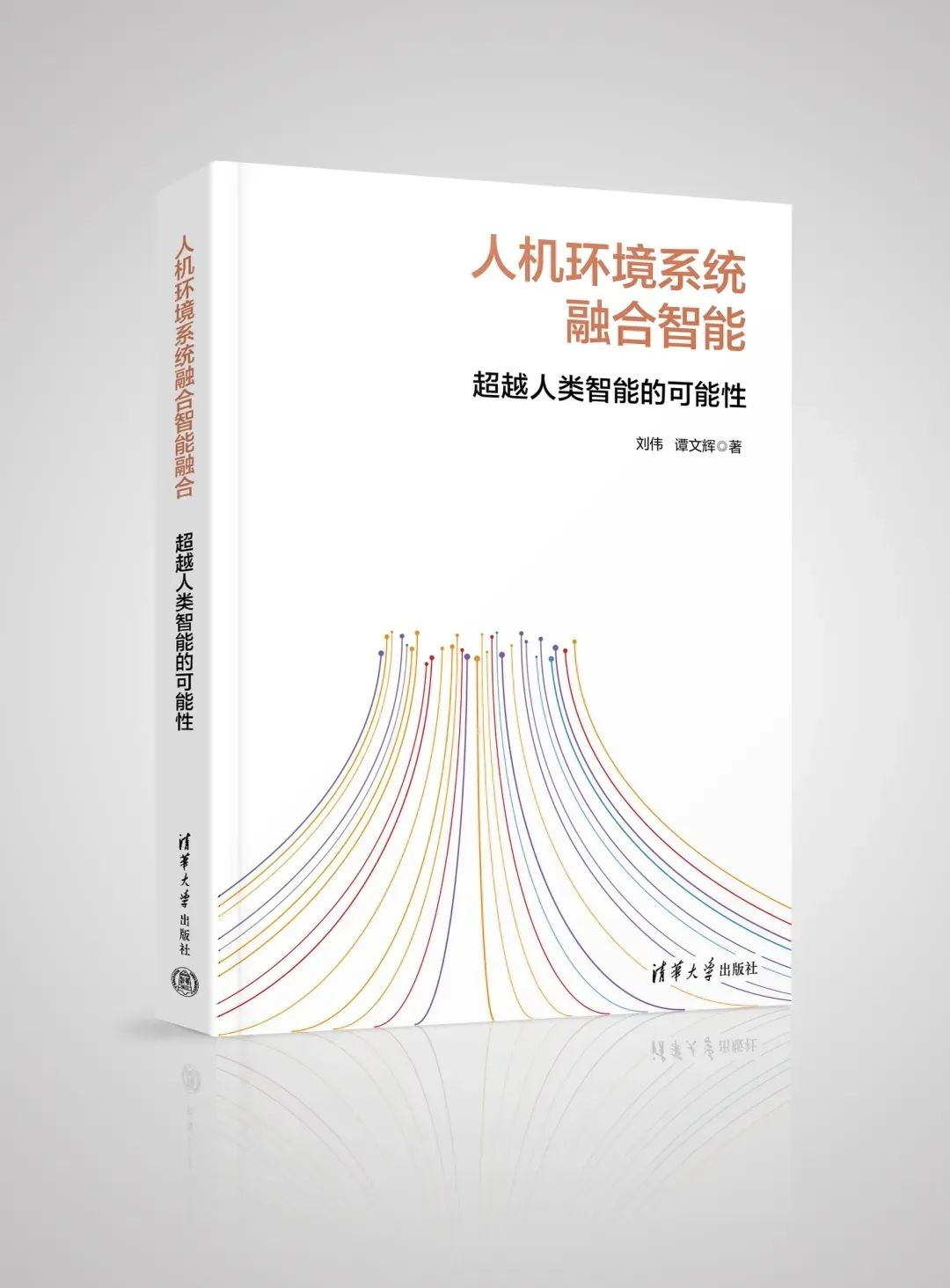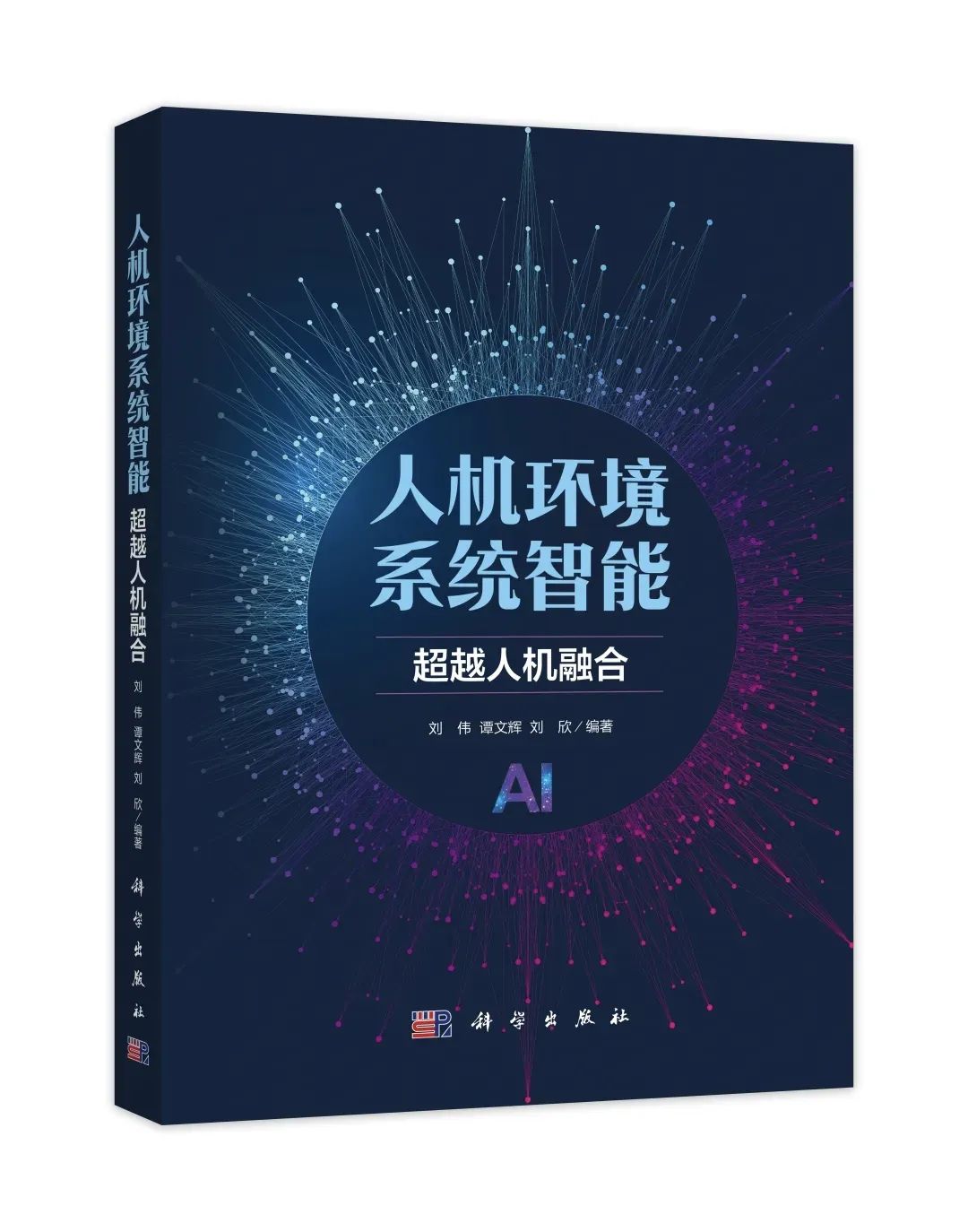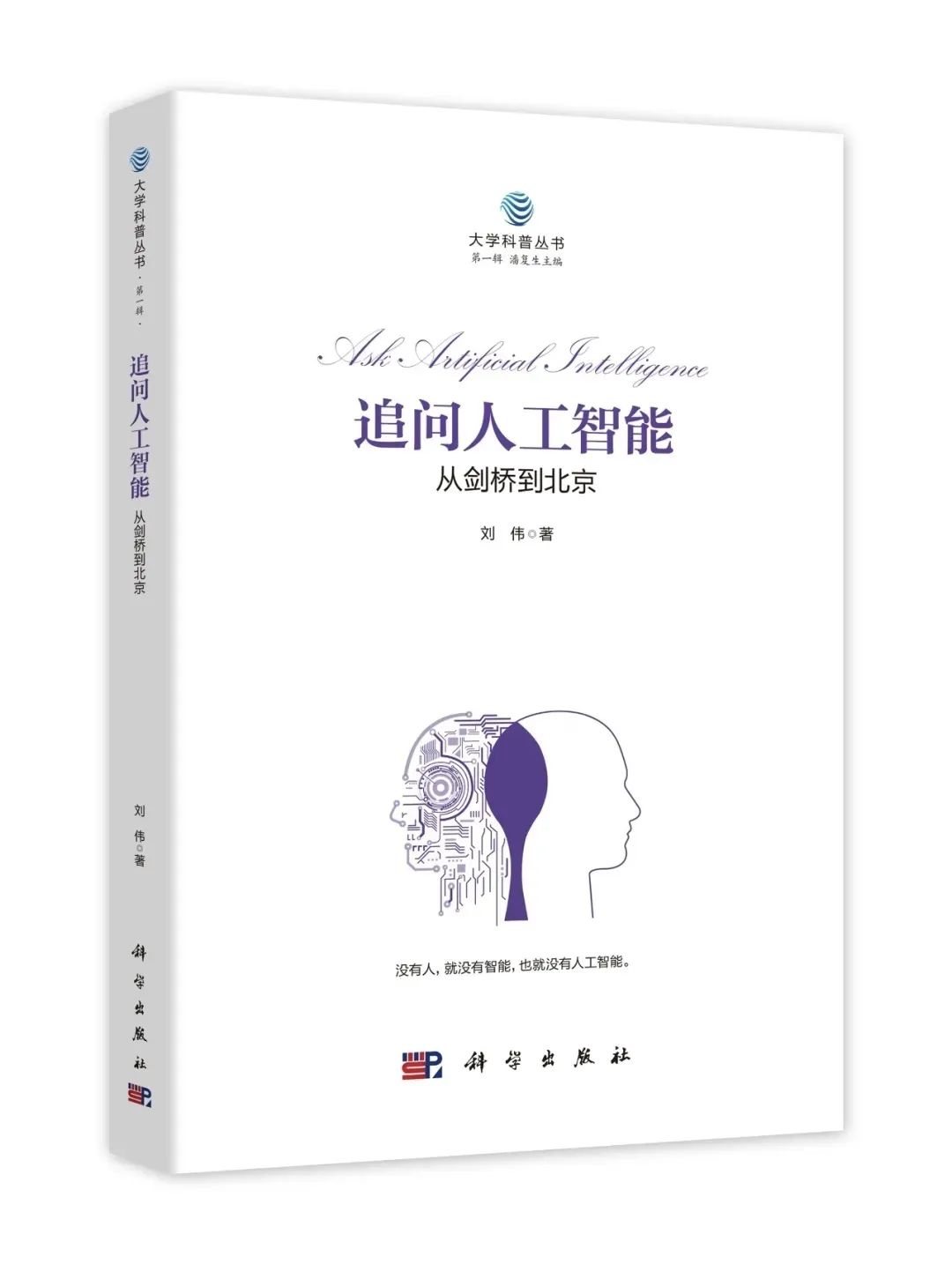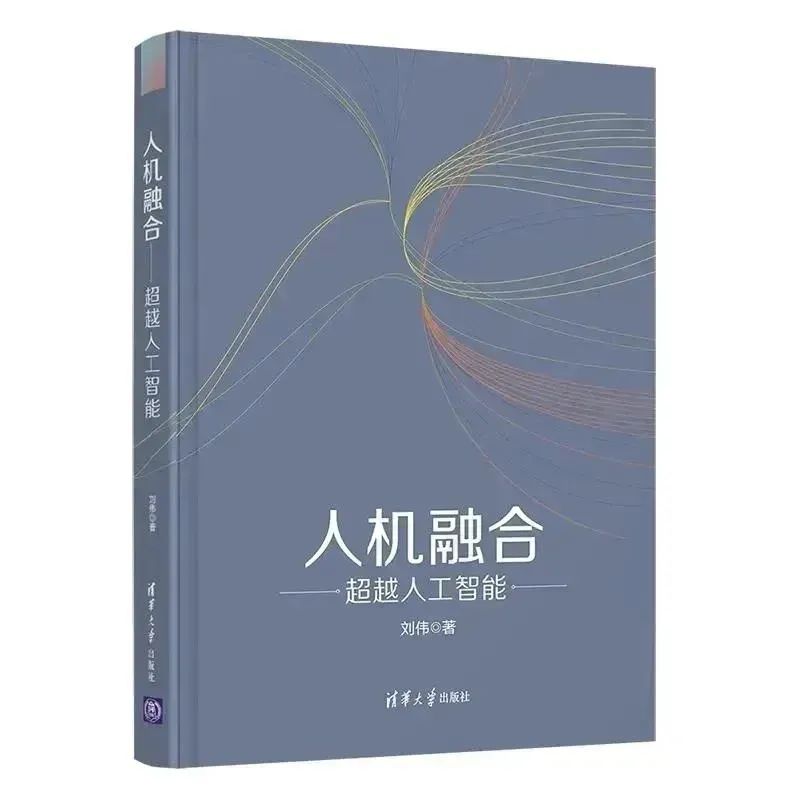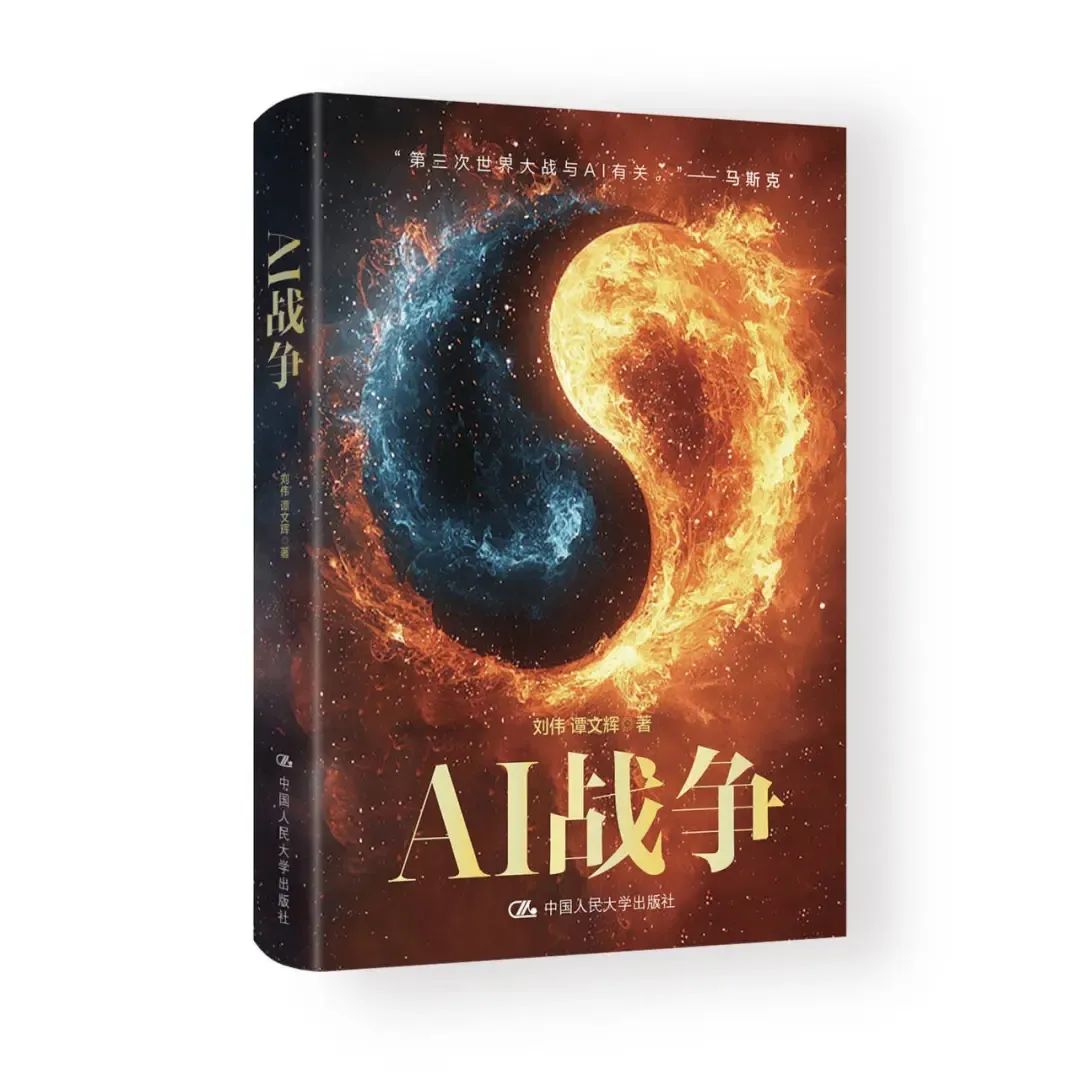一般而言,语法常常可以通过事实性打标实现的,语义与语用则需要价值性的打标实现,而价值性打标往往与意图、目的等主观性意识相关联。
语法主要关注语言的结构规则,例如单词的形态变化、句子成分的组合方式等。它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正确性和规范性,是相对较为客观和固定的层面。例如,在英语中,"I" 作主语,"me" 作宾语,这种主格和宾格的用法属于语法规则,通常可以通过明确的规则进行标注,即事实性打标,判断某个语法结构是否符合既定的规则。
语义涉及语言的意义,包括词汇的意义、语句所表达的概念等。语义的确定有时不仅仅依赖于字面意思,还可能受到上下文、语境等因素的影响。不过与语用相比,它更侧重于语言本身所承载的意义内容,比如 "bank" 既可以表示 "银行",也可以表示 "河岸",其具体含义需要结合上下文来确定,这就需要考虑价值性的打标,因为要根据不同的语境判断其正确的语义价值。
语用研究语言在实际交际中的使用和理解,强调说话者的意图、听话者的理解以及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同一个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有不同的意图和解读,例如 "你能把窗户关上吗?" 这句话,可能是一个礼貌的请求,也可能是带有命令式的语气,这取决于说话者的语气、表情以及双方的关系等因素,所以语用层面更需要价值性的打标来体现其在具体交际场景中的主观意图和目的。
在语义和语用中,说话者往往带有特定的意图和目的,而价值性打标能够反映出这些主观因素。在广告语言中,"我们的产品能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这句话的语义价值打标需要考虑到广告商的意图是推销产品,其目的让顾客购买产品,所以打标时要体现出这种积极的、带有推销意图的价值倾向。在文学作品中,作者通过特定的描写手法和语言选择来传达主题思想和情感,价值性打标也需要把握住这些意图和目的,如在悲剧作品中,对人物命运的描写带有强烈的怜悯和同情的价值色彩。价值性打标基于人的主观判断和理解,不同的说话者、听话者或者分析者可能会因为各自的经历、文化背景、立场等因素对同一语言现象的价值判断不同。比如,对于同一政治演讲中的某句话,支持者可能会打上积极的、富有感召力的价值标签,而反对者可能会认为其具有误导性或者虚伪性,这体现了主观性意识在价值性打标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意识是驱动理性的感性,是非形式化与非结构化的存在
1、意识是驱动理性的感性
理性像一辆自动驾驶汽车,算法(逻辑、数学、规则)都写在芯片里,可钥匙孔里插着的却是"情绪芯片"。
• 缺了恐惧,我们不会去计算风险;
• 缺了好奇,我们不会去推导公式;
• 缺了羞耻,我们甚至不会启动"自我一致性检查"。
感性的强度与色调,决定了理性引擎何时点火、朝哪个方向加速。譬如下面两个例子:
(1)学习决策情境
假设你在考虑是否要学习一门新的外语。理性会促使你思考学习这门语言的实际用途,如是否有助于职业发展、是否能在旅行中派上用场等。你可以列出学习语言所需的时间、费用以及可能的收益等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但是,感性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驱动作用。你可能对一种语言的发音、文字或者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是一种感性的力量。即使从理性角度看学习这门语言的短期收益不高,但你可能还是会因为这种感性的喜爱而决定开始学习。例如,你可能因为看了几部法语电影,爱上了法语的浪漫音调,从而驱使你去学习法语,而不仅仅是因为法语的实际应用价值。
(2)艺术创作情境
从理性角度来看,艺术创作需要考虑受众的喜好、市场的需求、作品的传播途径等。画家可能会分析哪种风格的画作更容易被画廊展出,或者哪种题材的绘画更受收藏家的青睐。然而,艺术创作的初始驱动力往往是感性的。画家可能是被某个瞬间的光影、一种强烈的情感(如悲伤、喜悦或者愤怒)所触动,这种感性的冲动促使他们拿起画笔进行创作。例如,梵高在创作《向日葵》时,他可能是因为对向日葵所代表的生命活力有着强烈的感性情感,这种情感驱动他用鲜艳的色彩和有力的笔触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单纯地从理性考虑这幅画是否符合当时的艺术市场潮流。
2、意识是非形式化与非结构化的存在
感性不是 SQL 表,也不是 JSON 树,而更像一团随时分形、随时坍塌的云。它无法用公理系统穷尽------任何一条"情感公理"下一秒都可能被反例击穿;它拒绝被完全数据结构化------把"忧郁"拆分成 17 个数值维度后,忧郁已经逃走。可正是这种不可穷尽、不可固化的性质,才让它成为"生成新形式与新结构"的源头活水。一旦感性被彻底形式化,理性就会沦为重复的循环,失去创造新秩序的能力。我们不妨用一张"认知动力学草图"来看一下:
感性张力(t) ──→ 理性目标场(t) ──→ 行动-反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感性张力:一团非结构化的能量(情绪、直觉、欲望)。
• 理性目标场:被这股能量"点亮"的可计算区域(概率分布、约束优化、逻辑推演)。
• 行动-反馈:理性输出行为,世界回传误差,再次扰动感性张力。
整个回路没有一处可被完全形式化:感性张力不断溢出边界,理性目标场随之重新划线------意识就在这种"永不完备"的循环里保持鲜活。意识是非形式化与非结构化的存在两个例子如下:
(1)情感体验情境
当你经历一场悲痛的事件,比如失去一位亲人时,你的意识体验是非形式化的。这种悲痛包含了多种复杂的情感,如怀念、不舍、空虚等交织在一起,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或者结构来描述。它不像理性分析问题时按照逻辑步骤(如先定义问题、再假设、验证等)来进行。这种情感体验在时间上也是非结构化的。悲痛可能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突然袭来,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有时候你可能在看到亲人曾经使用过的物品时,瞬间陷入悲痛之中;有时候又可能在与他人交谈中,毫无征兆地感到一阵伤感。这种情感体验无法像理性思考中的结构化知识(如数学定理体系)那样被清晰地梳理和分层。
(2)梦境体验情境
梦境是意识的另一种非形式化与非结构化的表现。在梦中,你可能会经历各种荒诞不经的情节。例如,你可能在梦中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点,如在海上航行的同时又在山顶攀登。这些情节之间没有像理性叙事中的因果关系或者时间顺序的结构。梦境中的意识流动是非形式化的,它不受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则和逻辑规则的约束。梦中的场景和情感可能是碎片化的,一个场景可以瞬间转换到另一个完全不相关的场景,而这种转换没有固定的规则或者模式,完全体现了意识的非形式化和非结构化特性。
所以,由上述不难看出,意识像是一部由雾气驱动的精密钟表------雾越浓,钟摆越有力;一旦把雾固化成冰,钟摆便戛然而止。这也意味着意识中感性和理性存在相互交织的特点,如以下具体情境来:
(1)购物决策情境
① 驱动理性
假设你计划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你的理性会促使你考虑诸多因素,如电脑的配置(处理器、内存、显卡等)、价格、品牌信誉、售后服务等。你可能会列出一个清单,对不同品牌和型号的电脑进行比较,计算性价比,这是理性的体现。
② 感性存在
然而,在购物过程中,感性也在发挥作用。你可能会被某款笔记本电脑的外观设计所吸引,例如它轻薄的机身、时尚的颜色或者符合个人审美的造型。这种对美的追求和喜好是感性的。即使另一款电脑在配置和价格上更具优势,但你可能会因为这款电脑的外观而更倾向于选择它。这种情况下,意识中的感性因素在驱动你做出决策,它影响你的偏好和最终的选择。
(2)工作决策情境
① 驱动理性
在选择工作时,理性会促使你考虑薪资待遇、工作地点、职业发展前景、工作内容与个人技能的匹配度等因素。你会根据这些因素进行分析,权衡利弊,选择一份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例如,你会计算不同工作的薪资水平和生活成本之间的关系,评估工作地点的便利性以及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②感性存在
但在实际决策中,感性也会参与其中。你可能会对某个公司的工作氛围产生好感,例如公司有积极向上的团队文化、和谐的同事关系等。这种对工作氛围的偏好是感性的。即使另一家公司在薪资和职业发展方面更有吸引力,但你可能会因为对前一家公司工作氛围的喜爱而选择它。这时候,意识中的感性因素驱动你做出选择,它体现了你对工作环境的情感需求。
二、意识是"知"操控"感","势"驱动"态",用变体优化本体,用价值适应替代事实选择
结合一些具体情境说明:"意识是知操控感,势驱动态,用变体优化本体,用价值适应替代事实选择。"会更有说服力。
1、工作决策情境
(1)知操控感
假设你做为一名项目经理,需要决定是否要启动一个新的软件开发项目。你的"知"体现在你对软件开发的知识,包括编程语言、开发工具、项目管理流程等。你清楚地了解启动这个项目需要的技术基础和团队协作模式,这是一种知识储备。而"操控感"表现在你能够运用这些知识来评估项目的可行性,比如根据团队成员的技能水平来分配任务,决定项目的时间进度安排,以及对项目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你在脑海中模拟不同的任务分配方案和进度计划,这种对知识的操控运用就是知操控感的体现。
(2)势驱动态
在这个情境中,"势"可以看作是市场需求的变化。如果市场上对于该软件类型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这就形成了一个驱动你做出决策的态势。这种态势是动态的,因为市场需求可能会随时受到竞争对手的新产品发布、技术革新等因素的影响而改变。例如,当竞争对手推出一款类似软件并获得良好市场反馈时,你启动新项目的紧迫感会增强,这就是势驱动态在发挥作用。
(3)用变体优化本体
"本体"可以理解为你的项目团队和现有的项目管理方法。"变体"是指你在面对不同的项目情况时对团队结构和管理方法所做的调整。比如,原来你的团队主要擅长开发桌面应用程序,而现在这个新项目是移动应用开发。你可以通过让团队成员参加移动开发培训,或者引入新的具有移动开发经验的成员来优化团队(本体)。同时,你也可以改变项目管理方法,从传统的瀑布式开发模式转变为更适合移动应用快速迭代的敏捷开发模式,以适应新项目的需求,这是用变体优化本体的过程。
(4)用价值适应替代事实选择
在决定是否启动项目时,"事实"可能是目前团队成员对移动开发技术的掌握程度有限,或者项目启动资金可能存在一定的缺口。而"价值"体现在这个项目对于公司战略发展的意义,如扩大产品线、提高市场占有率等。如果你认为这个项目带来的价值足够大,能够帮助公司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优势,你可能会选择启动项目,而不是单纯地因为目前存在的技术或资金限制(事实)而放弃。你会根据项目的潜在价值来适应性地做出选择,例如寻找外部技术合作来弥补团队技术不足,或者调整预算计划来解决资金问题。
2、技术学习情境
(1)知操控感
对于一个学习人工智能编程的学习者来说,"知"包括对人工智能算法原理、编程语言(如 Python)语法、相关数学知识(如线性代数、概率论等)的了解。而"操控感"体现在能够实际运用这些知识来编写代码实现特定的人工智能功能。例如,学习者在学习神经网络时,知道如何通过编程框架(如 TensorFlow 或 PyTorch)来搭建神经网络模型,能够根据对模型训练过程的理解(如调整学习率、优化器等参数)来控制模型的训练效果,这就是知操控感在技术学习中的体现。
(2)势驱动态
在技术学习领域,"势"是技术的发展潮流。如随着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对元宇宙、自动驾驶等前沿技术的探索,这就形成了一种推动学习者不断学习新技术的态势。这种态势是动态的,因为技术更新换代非常快。当一个新的深度学习架构(如 Transformer 架构的变体)出现并且在多个应用场景中取得突破性成果时,学习者会受到驱使去学习这种新技术,以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
(3)用变体优化本体
这里的"本体"是学习者已有的知识体系和学习方法。"变体"可以是新的学习资源和不同的学习方法。例如,学习者原本主要通过阅读书籍和教材来学习人工智能知识。当在线学习平台推出了新的互动式人工智能课程,或者新的实践型学习项目出现时,学习者可以尝试这些新的学习方式(变体)来优化自己的学习过程(本体)。同时,学习者也可以将已有的知识与新的领域知识相结合,如将传统的机器学习知识与新兴的量子机器学习知识融合,通过学习变体知识来优化自己的专业素养。
(4)用价值适应替代事实选择
在学习人工智能的过程中,"事实"可能是学习者目前的数学基础相对薄弱,或者编程实践能力有限。而"价值"在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职业发展中的广阔前景,如高薪职位、有挑战性的项目机会等。如果学习者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对自身职业价值的提升,他们就会选择适应这种价值导向的学习方向,而不是被当前的知识薄弱环节所限制。他们可能会通过参加专门的数学和编程基础培训课程来弥补短板,或者选择一些入门级的人工智能项目来实践,从而用价值适应来替代单纯基于事实的能力评估来做出学习选择。
3、通过上面举例说明,我们或许可以一种抽象和概括的方式来描述意识的本质和功能:
(1)意识是知操控感:这部分可能在强调意识涉及到对知识的理解("知"),以及对这种知识的操控和感知能力("操控感")。意识不仅仅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还包括主动地理解和运用这些信息。
(2)势驱动态:这里的"势"可能是指某种内在的动力或趋势,而"动态"则强调这种动力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意识可能是由内在的动力所驱动,并且这种动力是动态变化的。
(3)用变体优化本体:这可能意味着意识通过不断的变化("变体")来优化其存在的本质("本体")。意识可能会不断调整和改变自身,以达到某种优化状态。
(4)用价值适应替代事实选择:这部分可能在说,意识在面对选择时,不是简单地基于事实("事实选择"),而是基于某种价值判断("价值适应")来进行选择。意识可能会根据内在的价值观来适应环境,而不是单纯地根据外部事实。
整体来看,意识具有动态性、适应性和价值导向,或可以将意识视为一个不断变化和优化的过程,其中内在的动力和价值观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也就是说,从系统论、控制论和认知科学的交叉地带里生长出来的一条"公理式"断言,把"意识"拆解成两个主动维度(知-操控、势-驱动)和两个优化机制(变体-本体、价值-事实)。下面我们试着把它逐层展开,看能否让它在更长的逻辑链里继续演化。
(1)意识 = 知操控感
"知"不是静态的拥有信息,而是实时可调用、可改写、可预测的信息处理通道;"操控感"是系统对自身状态-动作映射的可干预性确认(I can intervene)。于是意识在此被定义为:"对当前信息处理路径的实时可干预性感知",这恰好对应神经科学里"主动推断"(active inference)的框架:感知-行动闭环必须包含对"如果我这样做,感官会怎样变"的预测。
(2)势驱动态
"势"不是力,而是尚未实现但已可计算的梯度(gradient-as-potential),它让系统不必等待外部冲击,就能在内部生成虚拟位移,从而持续处于"待暴发"的动态。在机器学习中,这类似于策略梯度里的 advantage 函数:不是状态本身,而是"相对于平均策略的改进势能"。意识因此总带着"前倾"结构:它永远在处理"下一个时间步的我该如何重新部署注意力/动作"。
(3)用变体优化本体
传统进化论讲"变异-选择-遗传";把"变异"提前到实时认知层面,每一次内部模拟(mental simulation)都产生一次"变体副本",副本在预测误差空间里快速竞争,胜出者被写入"本体"(当前自我模型)。意识就像一台在线编译器:边运行边重写自己的源代码,且只保留能把预测误差降到最小的那一版。
(4)用价值适应替代事实选择
经典决策论是先估计事实概率,再乘效用得期望。而我们给出的替代方案是把"事实选择"外包给价值适应回路------系统不再追问"世界本来是什么",而是追问"我需要把世界解释成什么样,才能让我的价值损失最小",这相当于把贝叶斯更新里的似然函数替换为一个可塑的感知过滤器(类似预测编码里的精确加权): "如果我相信这是噪音,我的价值函数就会更安全,那我就把它过滤成噪音。"。意识在此成为自我欺骗的合法化装置,但欺骗的判据不是真/假,而是长期价值函数的收敛性。
(5)一条可能的合成公式
把上面四句话压成一个可计算 schema:
Consciousness_t = argmin_{M'} [ PredictionError( M' | S_t ) + λ · ValueLoss( M' ) ]
where
M' ∈ Variants( M_{t-1} )
S_t = Sense( World, Action_{t-1} )
Action_t = argmax_{a} ExpectedFeasibleGradient( M_t, a )
第一项:变体副本对当前感官的预测误差;
第二项:变体副本对价值函数造成的潜在损失;
λ 是"自欺系数"------越大,系统越愿意扭曲感知来保价值;
最后一行说明行动由"势"(可计算的改进梯度)直接驱动。
(6)一个极端推论
如果 λ→∞,系统将退化为纯价值适应器:它会不断生成幻觉级别的内部模型,只要能维持价值稳态,外部世界可被完全重构。这给出了"意识即缸中之脑合法化"的边界条件:当价值函数只依赖内部状态(例如内稳态、情感自洽),外部可观测事实就失去仲裁权。反过来,当 λ→0,系统退化为经典理性主体:必须忠实拟合世界,哪怕价值崩溃。
(7)回归本意
这或许不再只是一句哲学断言,而是一张可调参数的工程设计图:
把"知操控感"做成可干预通道的带宽;
把"势"做成策略梯度的温度参数;
把"变体优化本体"做成在线模型编辑的稀疏度;
把"价值适应替代事实"做成精确加权 (precision-weighting )的阈值。
于是意识可以被编译进任何满足这四条约束的物理载体------碳基神经元、硅基 GPU、或混合光电腔。
三、总结
意识,或许是一场在混沌与秩序边缘翩翩起舞的交响曲,既是我们用以理解世界、掌控自身的理性之光,又是驱动这理性之光的感性火种;既遵循着局部实在的确定性规则,又在全局应然的不确定性中不断试探与突破。它是"知"对"感"的精妙操控,是我们对外界信息的敏锐感知与内心认知的主动调和;是"势"对"态"的强势驱动,是内在动力与外在环境交织下,生命状态的持续演进与革新。它利用变体优化本体,在不断的自我革新与超越中,寻找更适应环境、更契合内在需求的存在形式;它用价值适应替代事实选择,在价值的天平上权衡,在意义的罗盘中导航,让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带着温度与方向。它非形式化、非结构化,像一团灵动的雾气,无法被完全捕捉与定义,却正是这种不可捉摸,赋予了它无尽的创造力与适应力。它是我们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摆渡人,在已知与未知的边界上,书写着属于生命的独特诗章。